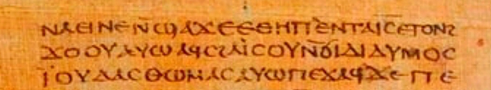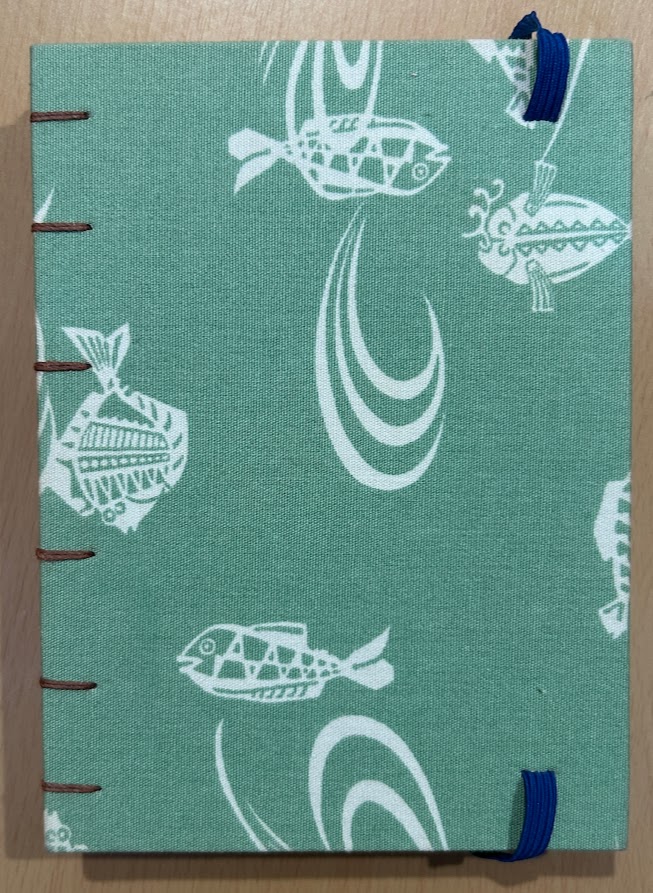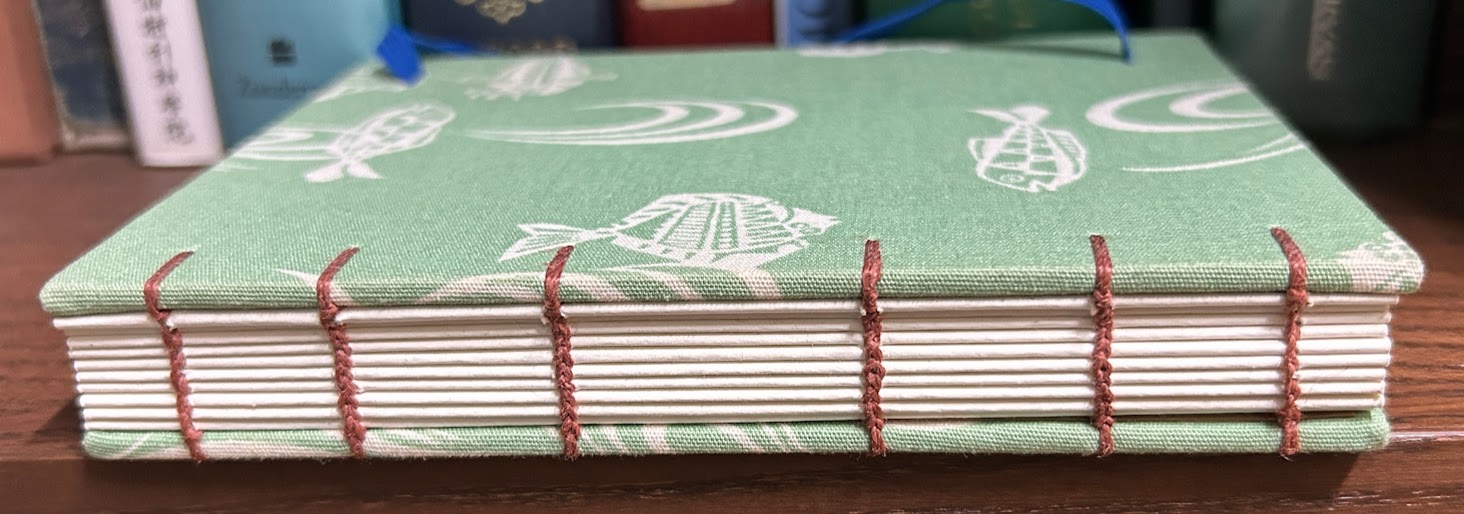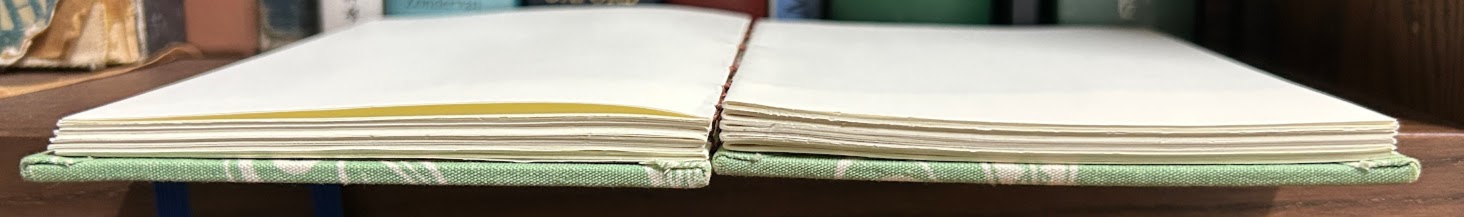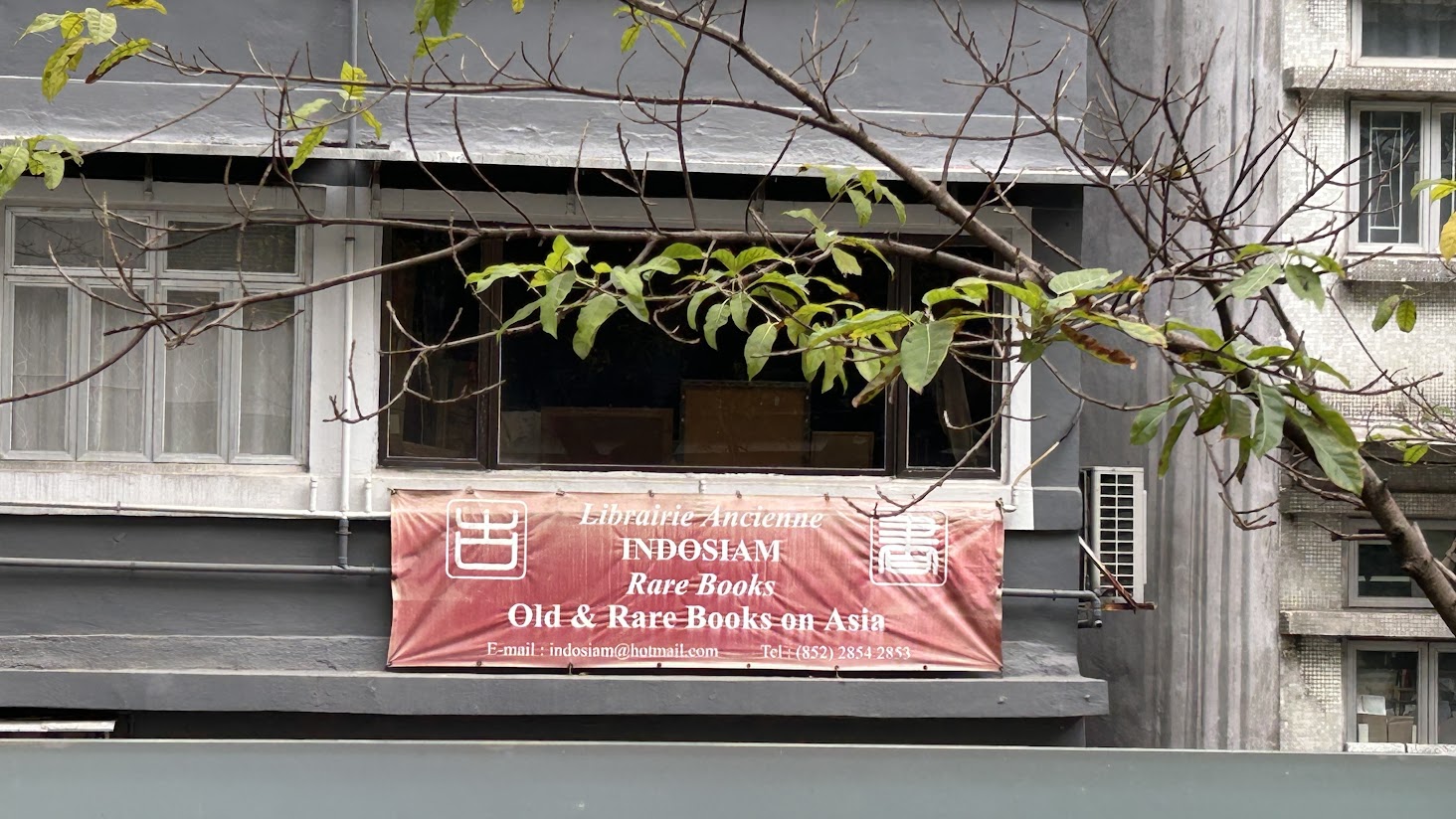特特特案:我只是討論歷史,跟搭巴士扣安全帶的法例無關。在紐絲綸,巴士好像沒有安全帶的,最近在紐約搭過一次巴士也是沒有的。其實,在紐絲綸不守規矩不依燈號過馬路的大有人在。我秉承中國香港的守法精神,嗤之以鼻。
日本學者滋賀秀三認為,清代縣官判案是情理兼備,並非一斷於法。美國學者黃宗智則認為,清代縣官是依法判案的,並以檔案為依據。不過,黃宗智也同時提出清代司法有第三領域,即動員社會宗族等力量調解糾紛,免得對簿公堂。我依託這些觀念來研究教案,希望在夾縫中找到一點新見解。
清代縣官,是一人政府,要自費組織班底;而且三權獨攬,是地方行政長官、財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驗屍官、法官、…,無所不包。清代的司法制度嚴謹,接到案件後要在五天內決定是否受理,一般戶婚田土等細事二十天內要審結,每月向上級呈報,所以工作繁忙。所以,縣官是討厭訴訟的,撤控、和解、私了等最為理想,雖然犯法就是犯法,但法外有情、法內有情,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是最佳出路。
不過,這是舊時代了,新時代是依法治國,追究到底,人情是干預司法的負面因素,應提倡袖手旁觀,鐵石心腸,無動於衷的精神。
商君書賞刑篇謂:「聖人之為國也,壹賞,壹刑,壹教。」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