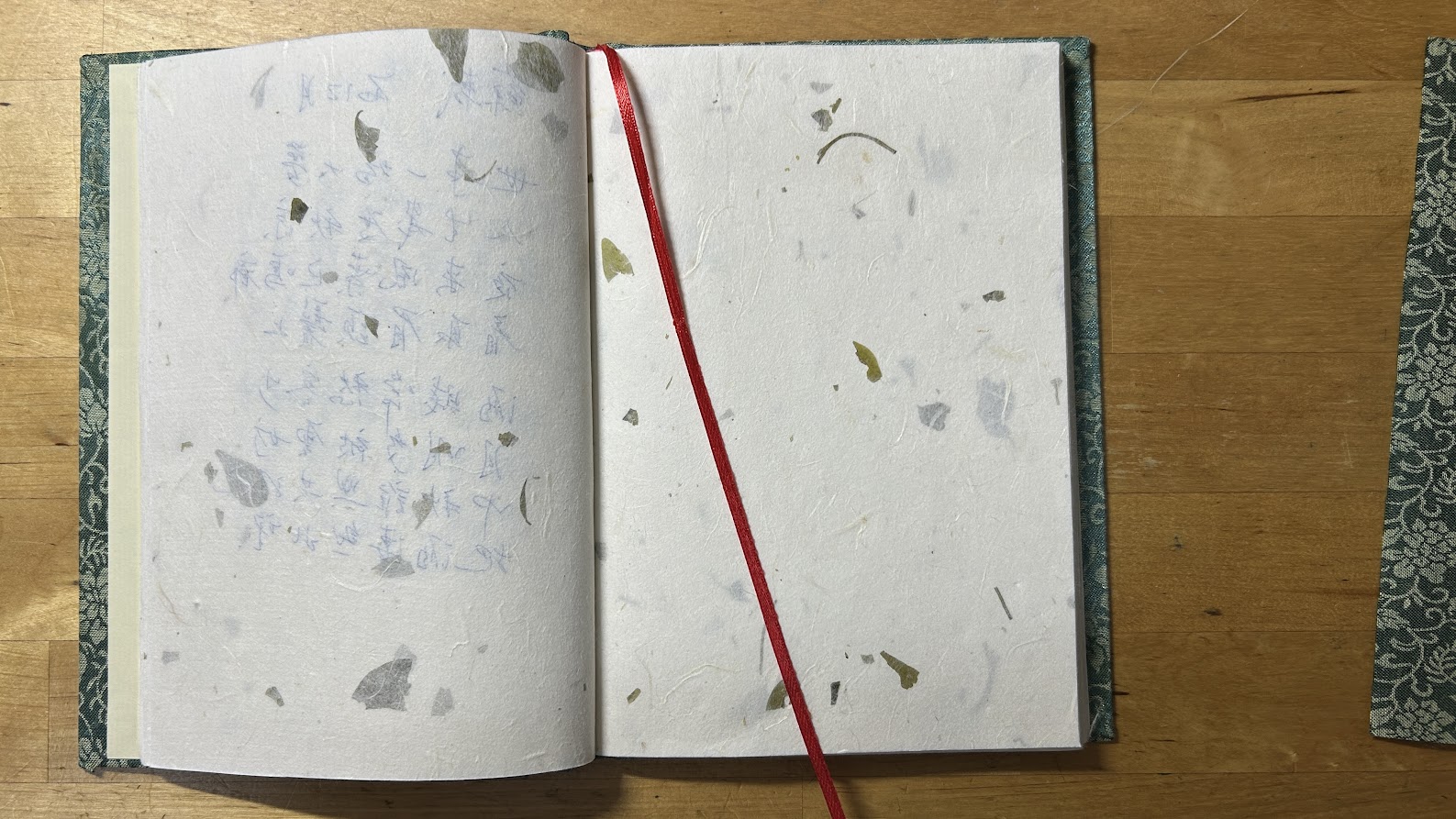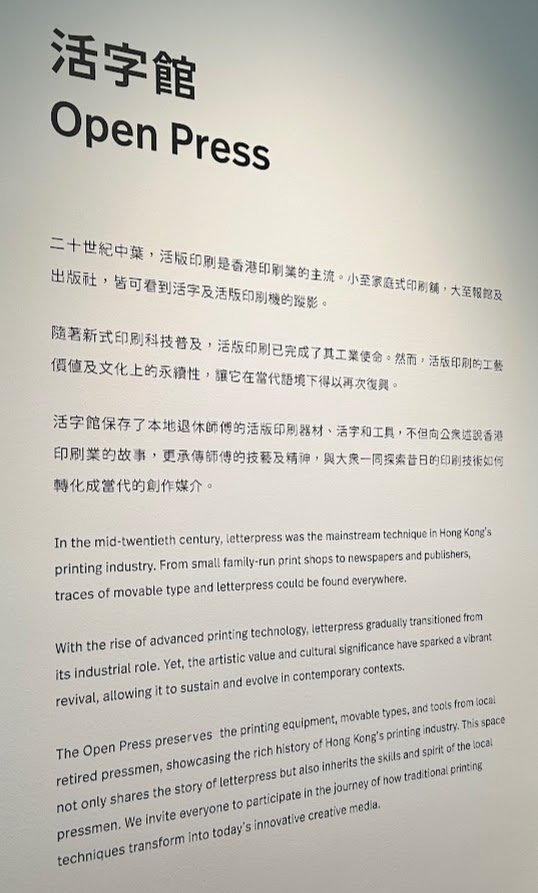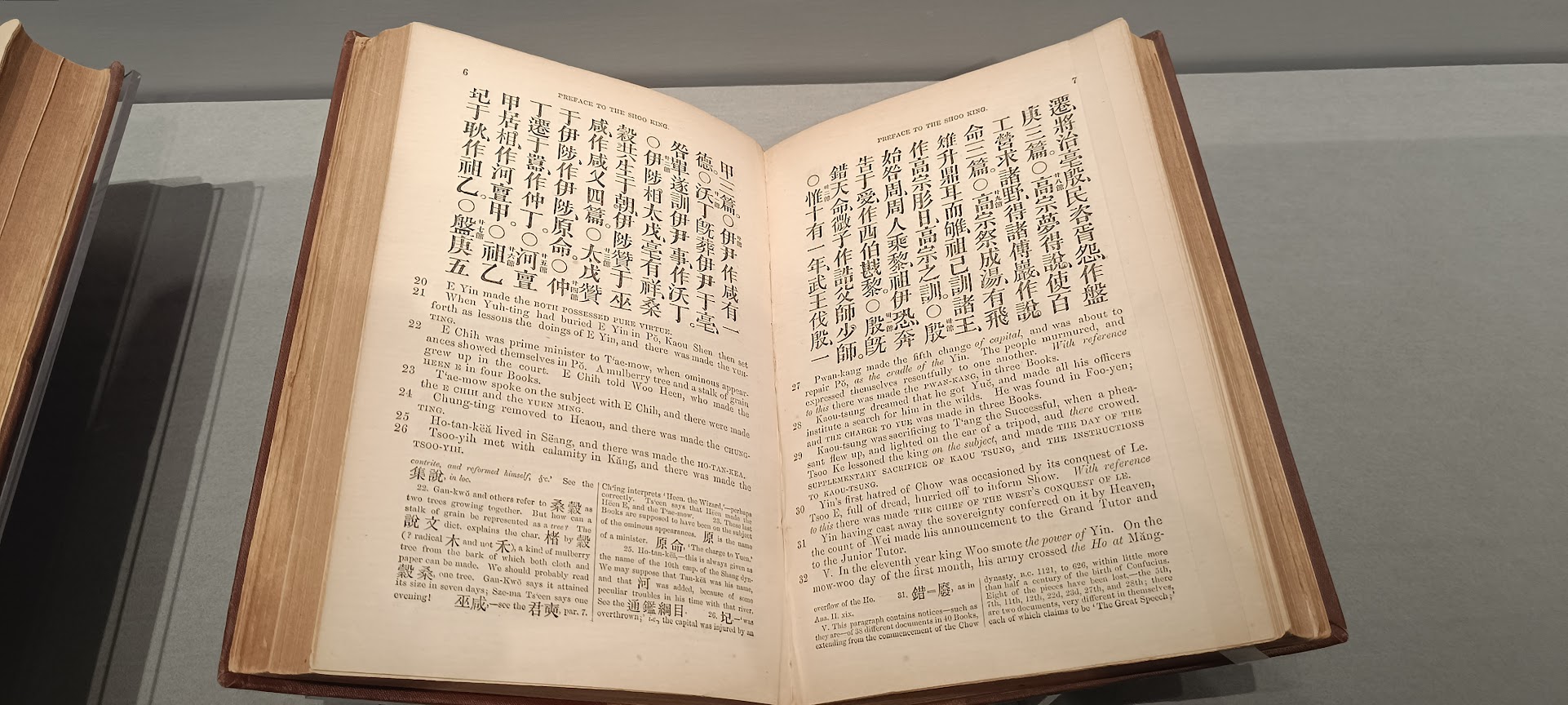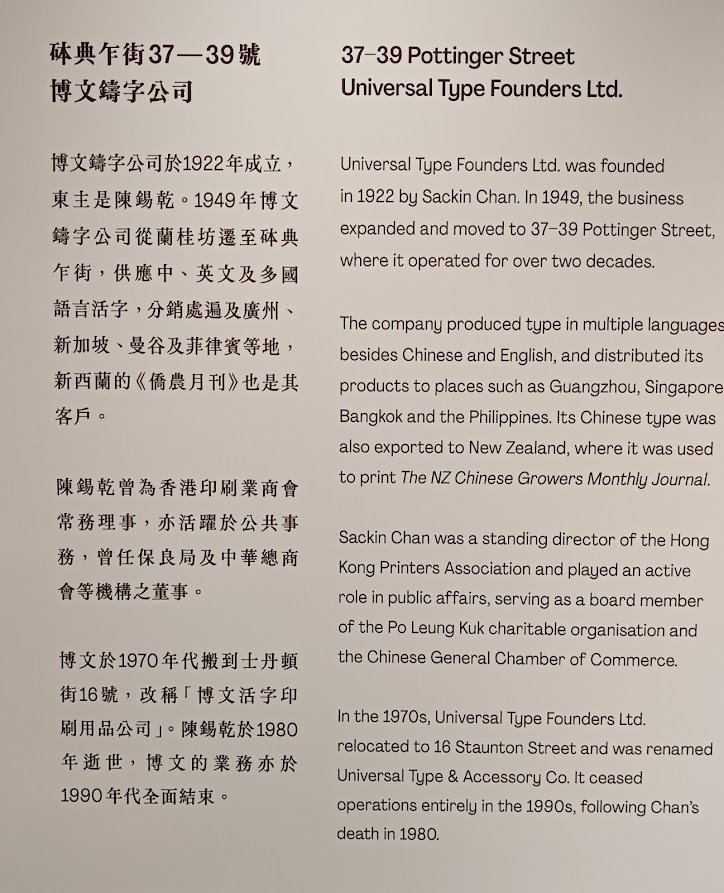今早看到這一段文字,是潘霍華《獄中書簡》的一段文字,十分精采:
“The fact that the stupid person is often stubborn must not blind us to the fact that he is not independent. In conversation with him, one virtually feels that one is dealing not at all with him as a person, but with slogans, catchwords, and the like that have taken possession of him.” (Bonhoeffer, “On Stupidity”,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恭錄宇宙最強 DeepSeek 的中譯:
「愚昧之人往往固執,但這不應使我們忽視他其實並不獨立。與之交談時,人們幾乎感覺不到是在與一個有主體性的人對話,而是在與那些佔據了他的口號、套話之類的東西打交道。」
潘霍華論的,是針對那些在希特拉時代信了希特拉那一套的精英有感而發,他們都是聰明、有學問、善良、敬虔的人,卻喪失了獨立思考,變得愚蠢。我請宇宙最強 DeepSeek 譯出全段,毋須核對原文,必然正確無誤。重要的話要講三次:潘霍華講的是希特拉時代的德國人。潘霍華講的是希特拉時代的德國人。潘霍華講的是希特拉時代的德國人。他不是先知,不是說預言;至於歷史會否重演,時地人事早已不同,那是哲學問題;至於潘霍華是否具先知式的洞見(Prophetic insight/Prophetische Einsicht/Intuitus propheticus/Perspicacité prophétique),那要到世界末日才可知道。
八十年代,基督徒都在談潘霍華,應該說,選擇留的都談他;在新時代,由治及興,我反而沒有再聽過他,可能,去與留已不用選擇了,誰還有興趣讀潘霍華。
至於我,只想遠離世界,走進沙漠,選個山洞,終身修行,做 hermit。
《論愚蠢》
愚蠢之於良善,是比邪惡更危險的敵人。邪惡尚可抗爭,能揭露其面目,必要時甚至以武力制止。邪惡總會自掘墳墓,至少會使人不安。但對愚蠢,我們束手無策。抗議或武力皆無效,理性說服徒勞;與個人偏見相悖的事實,愚者或嗤之以鼻,或斥為虛妄,即便鐵證如山,也可輕蔑視為無關緊要的個別事件。因此,愚者與惡棍不同,他們自滿至極,甚至極易變得危險——稍加挑動便顯露攻擊性。對待愚者,須比惡棍更謹慎;我們絕不該再試圖以理服之,因這既無益,更招險。
若要應對愚蠢,必先理解其本質。可確定的是,愚蠢是道德缺陷,而非智力不足。有人思緒敏捷卻愚昧,有人遲鈍卻絕非愚者——這發現常令我們在特定情境下驚愕。由此可見,愚蠢非天生,而是後天習得:人們或因自身言行,或因他人誘導而陷愚。更進一步觀察,孤僻獨處者較少見此缺陷,反見於熱衷或被迫群居的個體與群體。愚蠢因而更屬社會學問題,而非心理學範疇;它是歷史境遇作用於人心的產物,是外部因素催生的心理副產品。
細究之,任何權力的暴力展示——無論政治或宗教——皆會引發大規模愚蠢的爆發。這儼然是心理與社會的定律:權力需要愚蠢為其服務。並非人類的智力等能力遭扼殺,而是權力的膨脹令人喪失獨立判斷,甚至不自覺地放棄自主評估新局勢。愚者常顯頑固,但切勿誤解為獨立。與之交談時,你感覺面對的並非他本人,而是佔據其心智的口號、套話之類。他如受蠱惑,目不能視,本性遭扭曲利用。淪為被動工具的愚者,既能行萬惡,又無法辨識惡之所在。此即惡魔式操控的危險,其對人性的摧殘無可挽回。
但此刻亦清晰可見:愚蠢無法靠說教克服,唯有「解放」能終結之。因此我們必須認清,多數情況下,內在解放需以外在解放為前提;在此之前,試圖說服愚者純屬徒勞。此情境中,探問「民眾真實想法」毫無意義,對負責任的思考與行動者而言,這問題根本多餘——當然,這一切僅限於特定條件。聖經有言:「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詩篇》111:10),意指唯有在上帝面前活出負責任的生命,獲得內在解放,才是根治愚蠢之道。
關於愚蠢的思考亦存慰藉:它絕不意味多數人在任何情況下皆愚昧。關鍵在於,掌權者究竟期待從人民的愚蠢中獲益,抑或珍視其智慧與思想獨立。